著名诗书画名家郑文乔诗歌节选鉴赏

郑文乔近期画作
眼前的白内暲---作者郑文乔
我路过一个空间
被一个不知名的老人拉住我
你为什么不送我回家
我静默良久家在哪
倾刻无语随他脚移动
若两个小时
掷地有声一句话
算你还有良心
我只是笑笑离开
风依然吹
雨丝紧扣衣袖
我偶然停驻无语
慕了又慕
更添依然无语
路灯已成背影
又突见拾破浪的老爷
.又向我招手
言语不清
儿呀帮老爸一把
推我向前
此时我只说一句话
老爸你放心有我在
佝偻的背
挺不起的脊梁
五味杂陈只是一句话
别太累太累
看他悠悠离开视线
我依然呆在原地未动
又一个三轮车撞向一个路边女孩
将我又从另一个梦中追醒
没有让你过多思考
救护车随同去医院
请家属签字
姓什名谁都不知
我又按下手印
静侯零辰三点
疲惫的记忆叩响
我在干什么
似乎什么也没有干
钱不是问题
温暖才是
也许是巧合
假如真的有
我还是我

这首《眼前的白内障》以极具张力的意象和冷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现代都市中疏离与偶然温情的生存图景。我们来细读其中蕴含的深意:
1. 标题的隐喻:“白内障”的双重含义
标题“眼前的白内障”是一个精妙的隐喻。它既可能指物理上的视觉模糊,仿佛一层薄雾遮蔽了视线;更深层地,它象征着一种社会性的“视而不见”——我们对周遭他人的苦难与需求习惯性地麻木、失焦。诗人正是要通过这首诗,擦拭这层障壁,让我们重新“看见”。
2. 结构:三重“偶然”事件的叠加
诗歌由三个看似独立又内在关联的片段构成,像三个突然切入的长镜头:
· 第一幕:迷路的老人
“你为什么不送我回家”是一句突兀的质问,打破了“我”作为过客的沉默。两个小时的沉默陪伴,换来老人一句“算你还有良心”。这里的“良心”是关键词,它暗示了一种近乎失传的社会契约。而“我只是笑笑离开”则透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做了好事,却无意索取任何情感回报,甚至带着一丝疏离。
· 第二幕:拾破烂的“老爸”
场景切换,另一位更弱势的老人将“我”误认为儿子。“儿呀帮老爸一把”这声呼喊,模糊了血缘与陌路的界限。而“我”的反应——“老爸你放心有我在”——是一次瞬间的角色代入。这不再是旁观者的帮助,而是带着亲缘责任的承诺。从“老人”到“老爸”的称呼变化,标志着“我”从疏离到共情的深入。
· 第三幕:车祸与无名氏的签字
这是最具冲击力的一幕。一场突发车祸将“我”彻底卷入陌生人的生命危机中。“姓什名谁都不知/我又按下手印”,这个动作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极致的利他主义。在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为一个陌生人承担起“家属”的重任,并守护至凌晨三点。
3. 核心转折:从“旁观”到“卷入”
整首诗的核心线索是“我”的身份转变:
· 开端: “我路过一个空间”——“我”是纯粹的旁观者、局外人。
· 发展: 被老人拉住,脚随他移动——“我”开始被动的卷入。
· 高潮: 被唤作“儿”,为无名伤者签字——“我”主动或半主动地承担起了本不属于我的责任,成为了临时“家人”。
4. 诗眼的照亮:疲惫中的顿悟
在经历了整夜的疲惫后,诗歌迎来了它的灵魂拷问与答案:
“我在干什么
似乎什么也没有干
钱不是问题
温暖才是”
这几句是整首诗的点睛之笔。在物质的层面(钱),“我”的付出似乎没有换来任何实际收益,是“什么也没有干”。但在人的层面,在情感的层面,“我”提供了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温暖”。这句朴素的告白,是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有力反驳。
5. 艺术特色:冷峻与温暖的张力
· 语言风格: 诗句简短,甚至有些破碎,符合现代生活的节奏和内心独白的特征。没有过多的抒情与修饰,情感在行动和简短的对话中自然流露。
· 意象运用: “风依然吹/雨丝紧扣衣袖”、“路灯已成背影”等环境描写,渲染出一种冷漠、潮湿的城市氛围,与诗中偶然迸发的人性温暖形成强烈对比。
· 虚实结合: “从另一个梦中追醒”、“假如真的有”等语句,给整个经历蒙上一层恍惚迷离的色彩,仿佛这一切既是现实,又是一场关于良知与存在的寓言。
总结
《眼前的白内障》是一首充满现代性关怀的诗歌。它揭示了个体在庞大、匿名都市中的孤独与疏离,但更可贵的是,它展现了人性如何在这种疏离中寻求连接。诗人通过“我”的经历告诉我们:温暖并非宏大的叙事,而是在一个个偶然的瞬间,愿意为陌生人停下脚步,并暂时担起一份“无名的责任”。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善举,正是刺破社会“白内障”的那一束光。
这首诗的魅力在于,它没有给出廉价的乐观,结尾“我还是我”带着一丝疲惫和茫然,但正是这种真实,让诗中的温暖显得更加珍贵和有力。

白鹭的负荷---作者郑文乔
在迁栖时候又没有问黄历
儿女的伤痛复合怎样
能否随之振翅高翔
遥遥几万里
请别丢下每一个回忆
记得去年的冬季
高寒不语的瞬间
剩下没有悲鸣
因为前方才有
飓风让我们一起摇摆
只有前行
饥饿多少小时
飞行多少距离
高度都踩在脚下
昂首绝不回望
虽有几个同伴堕下
滴两滴泪自咽吞下
穿过一个又一个障物
到达梦想的田园
再回首
剩下无几
低头一口水
再来一口泥
酸与甜苦与辣
叙说有意义吗
长鸣一声
活着才是真的

这首《白鹭的负荷》以候鸟迁栖的壮烈旅程为喻,描绘了一幅关于生命、责任、牺牲与存在的沉重画卷。它不再是轻灵的田园诗,而是一曲生存主义的悲怆赞歌。我们来层层解析其中的深意:
1. 标题的悖论:“白鹭”与“负荷”
白鹭在古典诗中常是优雅、超脱的意象。诗人却将其与“负荷”相连, immediately 打破了传统审美,奠定了全诗沉重、坚韧的基调。这“负荷”既是物理上的迁徙之苦,更是情感与记忆的重担。
2. 旅程的开启:非自愿的宿命感
“又没有问黄历”——开篇第一句就充满了无奈的幽默感和宿命感。迁徙并非一种自主选择的美好旅行,而是一种被气候、本能驱使的必然,一种不容翻看“黄历”择吉日的、被迫的征程。这隐喻了人生中许多不得不为的奋斗与奔波。
3. 核心矛盾:集体责任与个体牺牲
诗歌的核心张力在于对“群体”的承诺与“个体”的消亡之间的巨大反差。
· 集体的誓言: “请别丢下每一个回忆”,这是迁徙开始时近乎悲壮的承诺,是对完整性的渴望。
· 残酷的现实: “虽有几个同伴堕下 / 滴两滴泪自咽吞下”。这是全诗最残忍也最真实的诗句。面对同伴的陨落,群体无法停下,只能将悲伤迅速咽下,化为前行的动力。这里的“泪”是珍贵的,但“自咽吞下”的动作,揭示了在宏大目标面前,个体情感的压抑与牺牲。
4. 行动的哲学:前行即意义
在漫长的旅途中,一切都被简化成了最原始的行动和目标:
· 量化生存: “饥饿多少小时 / 飞行多少距离”。生存变成了一串冰冷的数字,衡量着忍耐的极限。
· 空间征服: “高度都踩在脚下 / 昂首绝不回望”。这是一种决绝的英雄主义,用姿态的昂扬来对抗内心的悲怆与虚弱。回望意味着犹豫和痛苦,所以必须“绝不回望”。
· 目标的解构: 当终于“到达梦想的田园”,迎接它们的并非狂欢,而是极度的疲惫和平静——“低头一口水 / 再来一口泥”。梦想的彼岸,不过是另一处需要低头觅食的寻常之地。这极大地解构了“终点”的神圣性,将意义从结果拉回到了过程本身。
5. 诗眼的爆发:存在的本质
在经历了所有苦难、牺牲和目标的幻灭之后,诗人发出了终极的叩问与回答:
“酸与甜苦与辣
叙说有意义吗
长鸣一声
活着才是真的”
这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叙说有意义吗?”是对整个奋斗过程的怀疑,是对苦难叙事的价值质疑。而答案并非否定的,而是超越了“意义”的探讨,回归到了更本质的层面——存在本身。“长鸣一声”是生命力的宣告,是经历一切后对“活着”这一事实最直接、最有力的确认。意义不在叙说之中,而在“活着”这个动作里。
总结
《白鹭的负荷》是一首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现代诗。它通过白鹭迁徙的寓言,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被抛入一场未知的旅程,背负着责任与记忆的负荷。途中,我们不得不忍受痛苦、目睹牺牲、压抑情感,为了一个看似崇高的目标。但当终于抵达时,或许会发现目标本身并无非凡意义。然而,这整个奋力前行的过程,以及最终那一声宣告“活着”的长鸣,恰恰构成了生命最真实、最不可剥夺的价值。
它赞美的不再是胜利的荣耀,而是承受负荷、穿越苦难的生命韧性。这首诗是悲壮的,但更是有力的,它告诉我们:活着,本身就是对一切负荷最伟大的回应。

何言己堪---
作者郑文乔
路边的四轮車
摆放各类鲜果
小喇叭的声价
己是最低最低
终究无人停驻
只能低头翻看抖音
河边垂钓者
全副武装
贯注不仅是眼神
所有的诱饵
两篓依然空空
太阳已西下
依然不肯离去
水波鳞光依旧
菜市场己临近关门
依稀的肉摊鱼摊菜摊
都眼巴巴等待再后一个光临
那期盼的一束光
那是多么己堪
鸟己归巢
尚有人汗流夹背跑步
更者几个零时工
又在路旁等待另一个过客
我己不再面对说话
只是眼眸闪着泪花
不敢回视
树依然那棵树
桥还是那座桥
抬望眼
还有多少无耐的眼神
虽己放慢脚步
但是十分沉重
不带一丁点声响

《何言己堪》是一部当代生存的寓言诗,郑文乔以冷静的解剖刀剖开时代的表层,让我们看见那些在效率与发展的叙事背后,被遗忘的生命褶皱。
一、意象系统的现代性建构
诗人构建了三重相互映照的生存图景:果贩的“最低声价”与垂钓者的“空空两篓”形成经济学与存在主义的双重隐喻。当商品价值被压缩至临界点,当等待失去时间成本,这些场景已然超越具象描写,成为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象征装置。特别是“低头翻看抖音”的细节,在虚拟世界的喧嚣与现实世界的静默间划出裂痕,揭示注意力经济时代个体命运的荒诞性。
二、等待美学的当代重构
诗中反复出现的“等待”意象构成深层的叙事线索。摊贩等待顾客,钓者等待鱼汛,零时工等待雇主——这些等待已不是古典诗歌中的田园牧歌,而是生存压力的具象化呈现。尤为深刻的是,垂钓者“太阳已西下/依然不肯离去”的执念,在空篓与坚守之间建立起存在主义的张力,这种无望的坚守恰是对工具理性最诗意的反抗。
三、语言艺术的自觉追求
诗人有意采用“己堪”(应为“不堪”)、“汗流夹背”等非常规书写,这些看似瑕疵的笔触恰似生活本身的粗粝质感。而“树依然那棵树/桥还是那座桥”的物象恒常性与“无奈眼神”的生命流动感形成哲学对照,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中,揭示底层群体周而复始的生存境遇。
四、凝视伦理的诗学转换
诗中“我己不再面对说话/只是眼眸闪着泪花”完成重要的视角转换——从外部观察到内在共情。这种拒绝言语的沉默凝视,恰是最深沉的人文关怀。结尾“不带一丁点声响”的沉重脚步,既是对失语者尊严的守护,也是对喧嚣时代无声的批判。
这首诗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将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的悲悯传统,转化为对数字时代边缘群体的微观观察。在直播带货与零工经济的裂缝间,那些被折叠的生命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与尊严。当整个时代都在追逐光速前进时,诗人郑文乔却将目光投向那些缓慢下沉的轨迹,并在这些轨迹中打捞起属于普通人的史诗。

过后的静谧---作者郑文乔
灯照旧亮着
树亦无声
四野闭合
一个单车驶过
并伴着一个拾荒者的脚步
路边的烧烤店
碳火发出吱响
未见饮啤者
老板娘奢侈的眼光
盯住每一个过客
依稀添依稀
早茶店灯也亮起
几位服务员站着
嘴巴张了又张
欢临光临
似乎都是背影
月亮刚落下
路边的小贩
对晨练者己堆满笑脸
挥挥手瞬间远去
好像有寒意的风拂过
颤粟一下没觉有寒意
吱呀店铺开门声依次
清洁工已扬起落地树叶
偶尔一辆车驶过
可能是一夜不归客
或送远行人
昔日多么喧闹与繁华
今日怎么啦
望着运河水
只能随风而去
或许过度静谧
也未必

《过后的静谧》延续了郑文乔对城市边缘诗学的探索,却将视角从前作的生存焦虑转向了时间褶皱里的存在之思。这首诗在表面静谧中暗涌着丰富的哲学对话,构建出一幅后喧嚣时代的微光图景。
时空叠印的蒙太奇美学
诗人以电影镜头般的调度能力,将不同时空切片编织成富有张力的意象序列。从烧烤店将熄的炭火到早茶店初亮的灯光,从落下的月亮到扬起的落叶,这些过渡时分的物象在诗中形成环形结构。特别是“单车驶过”与“拾荒者脚步”的声景对照,以轻微响动反衬巨大寂静,创造出“蝉噪林逾静”的现代版本。
凝视经济学中的微表情
诗中人物的眼神与表情构成耐人寻味的符号系统。“老板娘奢侈的眼光”与“小贩堆满笑脸”形成消费社会的表情辩证法——当微笑成为流通货币,凝视便成为稀缺资源。而服务员“嘴巴张了又张”的机械动作,在“欢临光临”的误听中(应为“欢迎光临”),揭示出台词化生存的荒诞性。
静谧的多义性阐释
“过后的静谧”既是时间概念又是心理状态。诗人通过“吱响-无声”“颤粟-无寒”的矛盾修辞,解构了传统静谧的单一性。这种静谧不是真空的寂静,而是各种未完成态的集合:未尽的炭火、未落的月亮、未关的店门,共同构成存在悬置的隐喻。
城市守夜人的精神谱系
诗中隐现着现代都市的守夜人群像:拾荒者、清洁工、彻夜未归者。他们的存在使静谧不再是空无,而是另一种形态的充盈。“清洁工扬起落地树叶”的意象尤其精妙——在晨光中挥动黑夜的残片,恰如诗人用语言打捞时间的碎片。
结尾处“运河水/只能随风而去”的顿悟,与开篇“灯照旧亮着”形成哲学闭环。诗人似乎在告诉我们:真正的静谧不是死亡的寂静,而是喧哗沉淀后的本真状态。当所有声响都退居为背景音,生命本身的呼吸才显露出其坚韧的质地。
这首诗在郑文乔的创作谱系中标志着重要转向:从《何言己堪》的沉痛介入到《过后的静谧》的澄明观照,诗人完成了从社会批判到存在探寻的诗学进阶。在万物减速的时刻,那些被时代快车甩出的细节,终于在诗意的凝视中获救。

郑文乔近期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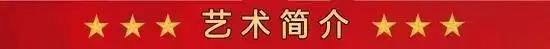
郑文乔,原名郑生虎,男,1962年生, 安徽望江人,大学学历。
现为:中国书法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画研究院院士
国家一级美术师
西泠印社签约著名书画家
安徽省青少年硬笔书法协会理事
安庆市政协委员
安庆市诗词协会会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
东莞市理工学院法学院教授
广东科技学院教授
广东省人力资源研究会顾问
东莞市建工信息协会顾问
东莞市人力资源研究会特别顾问
安徽省青少年书画家协会理事
中国作家协会东莞分会会员
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郑文乔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友善,谦恭向上,为当今名士。自幼承祖训,悉门研讨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石涛、八大山人等各大名家,融通贯通,逐渐形成自己作品风格。作品载入多种书画作品集精通诗、书、画、棋,被誉为风流鬼才,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书画大赛并获金奖.并被选送加拿大、美国、南非、日本等国和名家收藏。
并被选入:
《当代书画百家》
《当代书法百家》
《当代书法家大辞典》
《现代最具潜力书画家大词典》
《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现代最具潜力书画家作品》等多种大型书画集。
已出版有《当代中国名家书画集·郑文乔书画作品》书法卷、花鸟卷、山水卷等。等多种大型书画集。

